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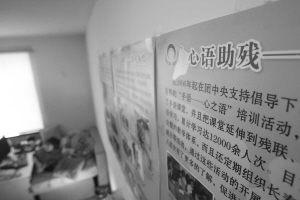 |
作为一个公益组织,心语协会并没有为自己“成人礼”做庆祝的准备,但是一些变化渐渐地融入岁月。“心语要进入后于海波时代了。”于海波拿过手边的水杯,慢慢地喝了一口水之后说,自己退休之后,有大把的时间回顾自己的心语的往事。但是在这之前,于海波要把她的个人号召力从心语抽离:“做公益要有制度化保证,而不是靠某个人的号召力。”于海波说,这个制度能正常运转的根本,是人们还没有形成的一个观念——公益成本。
横在协会制度之前的
“公益成本”瓶颈
“心语的现在是人治,以后要‘法制’。”于海波笑着对记者说。从当初那一部“心语热线”电话到现在的心语志愿者协会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9名专职员工,于海波渐渐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过往,而是一步一步地为自己的“退休”做着准备。“我都想了,等把所有工作都交出去之后,我最多也就是一个荣誉理事什么的。”于海波说,她已经渐渐地进入了幕后的角色,用一些制度性的章程来让身边的伙伴成长——但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“我现在最多是思考怎么能让心语健康地走下去。”于海波说,对于一个机构来说,肯定是要有开支的,这也是让她一直纠结的公益成本问题。
“现在心语接受的捐助,都是直接针对被捐助人的。”于海波说,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她给记者举例子,比如一笔助学捐款到位之后,协会都会对受助家庭进行走访、进行情况核实。然后在确定符合一定条件之后,才进行捐助。“我们一年要负责走访的贫困家庭有350-400个。”于海波说,每一次走访,最直接产生的费用就是交通费,而涉及到后期资料整理所需要的表格印刷等等,都是硬性的成本投入,“这一部分钱是捐赠人看不见的,但是的确存在。”于海波说,这一部分开支,心语没有权利从捐赠款项中抽取:“一码是一码。”
早些年,她会和一些大型商场、超市进行接洽,在这些地方放置捐款箱,但是渐渐的,这项工作无奈地终止了。“捐款箱每个成本800块,而每年一个捐款箱能募集到1000块左右的善款。”而这些善款最终都要用在受捐助人身上,但是捐款箱的成本,则需要心语自行承担。
“以前我也没意识到成本的问题。”于海波坦言,和很多做公益的机构、个人一样,她当年也并没有认为自己花一点钱能做到的事儿,在形成规模之后,会形成一个制约发展的瓶颈:“到了一定程度,就不是大家热热闹闹做公益的情景了。”所以于海波认为,有效的公益成本保证,是任何一个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下去的要件:“这不单单是有爱心就能解决的。”
基金会梦想
与现实之间的不等号
迄今为止,只有一名北京的慈善人士对于心语志愿者协会本身进行捐助。于海波告诉记者,这位在北京创业的吉林老乡,在2012年给心语协会捐赠10万元现金,今年捐赠数额将达到20万元。这位爱心人士明确表示,这些款项的捐赠对象是心语协会。“这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。”心语把这些捐款变成了必要的办公设施和人员开支。
现在心语志愿者协会有9名工作人员,他们每个月有1500元的工资,但这不是于海波心中的理想金额:“我觉得,协会的工作人员每月工资不应该低于1800元。”并且和工资并不对等的是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量,于海波告诉记者,按照现在协会开展的工作,需要15个工作人员进行满负荷运转,但是现在心语只有9名工作人员,“超负荷是一定的。”于海波坦承,这些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够留在这里,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情感在支撑,但于海波认为这肯定不够科学——任何一个机构能留住员工无外乎只有两个要件,适当的薪水和自身成长的机会,这是于海波的认知。
“现在协会的秘书长,在美国做访问学者,让她出去学点东西。”于海波认为,志愿者服务是个技术活,所以他们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一直贯穿在志愿服务的始终,但提到适当的薪金保证,于海波只能说这还没达到自己的心里预期。“一切的一切,最终还是要解决公益成本的问题。”
而现在心语积累自己自身经费,最主要的手段还是各种公益项目的承接。“在申请公益项目的时候,我们可以申请一部分经费。”于海波坦言,这部分经费,只能维持协会的日常运转,而不能实现心语的目标——开发自己的慈善项目。
在于海波的心目中,心语最理想的方式,是由志愿者协会变成基金会。因为政策规定,基金会可以拿出注册资金的10%作为运转资金,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运营,在增值的过程中,可以提高经费使用。“距离这个目标,心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于海波告诉记者,虽然这个目标堪称远大,但是心语一直做着准备。2009年,心语完成了“900”管理认证。针对申请基金会的前期准备工作,心语也一直在做:“我们现在能拿出10年以上的正规审计报告”,但是于海波又坦言,这些准备的前提要有注册资金,“针对心语的特点,注册基金会基本上需要200万的启动资金。”于海波说,心语现在肯定没有200万,即便有这笔资金,也是针对目标救助群体的专项资金,肯定不能用作基金会的注册。
旗帜性隐退
以及回馈社会体系
虽然公益成本的问题,现在仍然困扰着于海波,但是对于心语的发展,于海波认为:“我们大方向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。”于海波现在在一步一步筹划协会发展的同时,也在渐渐地从一个“旗帜性人物”向幕后隐退。于海波至今为止最骄傲的事情就是,以前一提到心语,大家都会说: “哦,于海波,知道。”但是现在一般提到于海波,大家都会说:“恩,知道,是心语志愿者协会的。”这种转变是于海波喜欢看到的。“制度才是第一位的。”于海波说,在制度的保障下,心语已经不再是于海波的心语,而对于自己今后的身份,于海波如此定位:“最多是个荣誉理事,但肯定不参与管理。”至于现在依旧没解决的公益成本问题,于海波说自己会努力,但是不强求自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
而在退休之前,有一个构想,于海波觉得自己可以达成。那就是针对受捐助者,建立一个回馈社会的服务体系:“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”。于海波觉得,这会从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——让受助者不能觉得爱心是自己应得的。
(记者 卢玉鸽/报道 董竞琦/摄)http://cswbszb.chinajilin.com.cn/html/2013-05/05/content_893708.htm
(于海波校友是北大心理系的学员,当时应该是和齐兵,姚思图尹大海同班的同学,据齐兵校友说,于海波结婚时,同学们曾出席婚礼。)